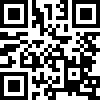陶渊明是东晋末年声名显赫的诗人,当官虽然没有当出名堂,但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已经广为流传了,归隐田园后,更是每日里与酒为伴,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田园诗篇。他在田园诗上的成就,即使是对于陶渊明的评价有欠妥当的南朝梁诗评家钟嵘,也给他作了一个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的定论。

而陶渊明极为好酒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,而且经常还能喝醉,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《饮酒二十首》组诗的自序中得到佐证:“偶有名酒,无夕不饮。顾影独尽,忽焉复醉”,总之是喝醉才能让他自己满意。难得的是他喝醉后还能写下不少名篇,这又是一大特点。今天介绍一首诗人数落儿子的诗篇,内容很是有趣,明明像在数落几个不成器的孩子,偏偏让人读起来像是在为他自己能多喝一口找的一个借口。

东晋·陶渊明·责子
白发被两鬓,肌肤不复实。
虽有五男儿,总不好纸笔。
阿舒已二八,懒惰故无匹。
阿宣行志学,而不爱文术。
雍端年十三,不识六与七。
通子垂九龄,但觅梨与栗。
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。
诗人写下此诗时应在44岁,而我们所熟知的《归园田居》五首以及《饮酒二十首》都是在其42岁起陆续创作完成,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,诗人嗜酒的帽子是一定摘不掉的了。诗人总共有5个儿子,他们的小名分别为阿舒、阿宣、阿雍、阿端以及幼子阿通。

虽诗名为《责子》,但我想诗人的是因为自己日渐衰老而发出的感慨。第1、2句说自己两鬓已生白发,肌肤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紧实。尽管才40多岁,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正是男子的壮年,但1600多年前的生活让他已然有了老者的模样。
第3至12句就完全在说他认为不成器的5个儿子了,由于诗句如同口述,简单直白,且一起将大意约略说明:我虽然有5个儿子,可没一个爱读书学习的。你看,大儿子阿舒都16岁了,最懒的就是他;阿宣也已经15了,舞文弄墨的事情跟他无缘;阿雍阿端这2个双生子13岁了,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;再说那小儿子阿通,话说也9岁了,孔融让梨这种事他不知道,成天登高爬低摘梨子摸栗子的事可一点没少干。

诗人出身名门,虽然家道中落,但几乎每一个有着祖上荣光的人都有着自己的傲气,就像诗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一般,对于读书这件事是一点也不会马虎的,所以他自己确实是读了不少圣贤书的,并且对于道家典籍也有所涉猎。不过到了他的儿子身上,似乎全然不是这么回事,这一点让诗人无可奈何。当当智能小程序
“乐享阅读季”来当当享特惠
最后我们的大诗人也是毫无办法,只好说,“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”,要是我家的天命就是这样,要让他们不学无术的话,那也就这样吧,不去说它,还是让我先喝点酒,消消这些愁吧。

你看,到了最后,诗人终于是露出了自己的“真面目”,他仿佛在找一个理由——并且他但凡有酒,似乎都要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喝醉,比如在《饮酒二十首·其二十》中有“若复不快饮,空负头上巾”,是说要是不喝痛快的话,实在有点对不起头上这头巾啊。关于头巾做滤酒巾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曾听闻,这也只不过是个痛快喝酒的由头罢了,因此诗人写这一首《责子》分明就有了“欲盖弥彰”之嫌了。
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诗人似乎对5子不肯读书的无可奈何,但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多的责怪之意,而是有着一股高人雅士的恬淡之气,又有着一股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诗人自身极为丰满的形象。

诗人明里在责子,实际上也是在表明自己的一种处事的人生态度,一切都不必太过功利,这首诗在最后2句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,若想进一步的话,诗人给几个孩子的家书《与子俨等疏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:他要的是自己的孩子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,贫穷与饥寒都无所谓,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具有高洁的品行,他自己也正是如此做的。
想,请点击上方,与我共同解读纯美古诗。